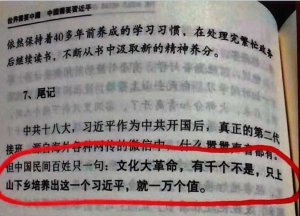郭沫若堪称中国的公知先祖。
国内网络上,最近出现一篇90后新秀的文章《知识人在政治反对中的自我定位》。作者韩乾,对中国的知识群体,提出鲜见的犀利见解。文章只有短短3千馀字,但却涵盖革命与改良、行动与言说、独立与中立、学理与心理等等许多公知大V都往往混淆不清的关键概念。全文通达流畅,说理层次分明,如此一篇好文,竟然出于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之手,不禁令人在赞叹后生可畏之馀,也凭空对未来多了一分乐观期许。
韩乾的文章提纲挈领,以政治反对为中枢立论,仅此一条就足以说明,作者对政治的认知水平,已超越国内的大部分公知。
所谓政治反对,即政治层面的反对意见或反对行动。按照从知到行、从弱到强的尺度,政治反对的具体实例,可以包括政治观念上的不同意,政治秩序上的不合作,政治议题上的抗议行为,以及政治制度上的否定或组党对抗。
政治反对的属性与强弱对比,直接反映了政治现实的生态,因此也是衡量体制形态的关键指标。如果现任政党与在野的反对党,共同均遵守民主法治的理念,在和平秩序下自由竞争,轮流执政,那么这就是常见的成熟民主。而如果当权党派占有明显优势,以专制性手段打压政敌,但反对派的地位仍受法律保护,并可参与选举竞争,那么这就属于竞争性威权。而如果政治反对,于行动层面被彻底消灭,于观念传播层面濒临灭绝,那么就属于极权或准极权体制。
以冲突博弈的角度来看,民主转型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在专制格局下,民主的政治反对,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而,恰恰是这一核心问题,多年以来,被中国的公知群体有意淡化回避,甚至刻意模糊扭曲,以至于国内在政治领域的公共话语,长期处于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境地,而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知识人在政治观念上的整体水平,极为低下。
以改良与革命的争论为例,韩乾在文章中指出,站在政治反对的出发原点,恳请专制自行退让的“温和”改良,与强行取消专制的“激烈”革命,本身只不过是政治实践中的策略选择,而并非政治反对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在逻辑上,如果“改良方案站不住脚,革命就必须成为一个选项”,反之亦然。但是反观中国的公知,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抱改良,反对革命。尽管某些公知,也许声称并不完全反对革命,但韩乾指出,这种单方面主张“倒逼”的改良理论,实际上等于为政治反对的规格设定上限,效果上仍然等同于否定革命选项。在韩乾看来,“仅从实践考虑,改良逻辑给行动者所设置的上限毫无道理”。
韩乾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公知的角色错位。公知只是理论言说者,而不是行动实践者。而政治转型,归根结底,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一点上,韩乾认为:“如果知识人不选择转换身份、参与抗争实践,那么他们就必须认识到,相对于行动者,自己仅仅是局外人:只有行动者才能决定抗争实践的具体策略。尽管局外人可以提出建议,但他们不应干涉局内人的行动,更不能认为自己有资格规制、导引局内人。”
然而很遗憾,绝大部分公知,受于身份的限制,决定了他们只可能是抗争的局外人。韩乾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也看出了问题的所在:“知识人是最脆弱的:他们一方面在生存上严重依赖于体制,另一方面却被要求有最高的独立性。这两点的冲突撕裂了他们”。更进一步,韩乾区分了独立与中立的不同:“这种独立性与中立的立场经常被人们混为一谈。实际上,在当下的政治态势中,独立性必定反对中立:如果独立性果真是知识人的美德,那么它就恰恰意味着不中立,亦即选择站在行动者一方。’中立’并非是非政治的,而是极为政治的:它恰恰是现代政治(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极权主义)不得不承诺与标榜的东西;既然体制承诺了中立,那么保持中立就是服从体制。”
极权体制下,独立必然意味着反对,而中立无非是顺从与默认的代名词。韩乾以如此年轻的头脑,便能深刻地体察到两者的根本区别,并且用简洁有力的话语表达出来,不得不令人大为赞赏。如果仅仅止步于此,韩乾的这篇文章,就已经可算作一篇上乘佳作。然而,或许正是因为头脑年轻,而免受于国内知识界的“烂污缸”之染,韩乾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巨大的根本性问题:“自我定位的问题对知识人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如上文分析所示,这种挑战并非是学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既然八九之后(乃至文革之后)的知识人境况不是学理所能解释的,那么今日的知识人的身份混乱就必定有其历史根源,并且,该根源将随着未来的体制变化催生更多非学理性的负面后果”。
正如韩乾所指出,公知在转型问题上无条件地排斥革命,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逻辑错误。而在现实中改良愿景一再破灭,公知们非但不从中承认理论的错误,反而拿着放大镜,极力寻找蛛丝马迹以自圆其说,甚至还有部分人士,沦落到编造宫廷阴谋论的低劣水平,完全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在政治话题上,自诩理性客观的公知群体,恰恰既没有理性,也极为主观。
尤其在近来乌克兰广场革命、台湾太阳花学运、以及香港占中等问题上,国内公知们的拙劣言论表演,不但显露出这个群体令人吃惊的知识结构缺陷,而且也更为清晰地说明,即便是在最低程度的观念抗争层面,在利益上直接或间接依附于体制的公知,也是如此地不堪一击,脆弱无比。
然而,如果仅仅从知识结构与利益驱使的角度,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公知群体,何以如此大规模的沦落不堪。毕竟,在当今获取信息,并不像过去那样困难。退一步讲,如果利益吸附,果真能够达到如此完美的笼络效果,那么类似于韩乾这样的80后90后的新秀知识人,又如何能在这种体制下,脱颖而出。
实际上,当下公知群体的堕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堕落,这个群体所折射出的,是对八九残酷的完全臣伏,以及被内心深处的恐惧情绪所彻底支配。在这种残缺的群体意识之下,公知们再也无法找到一个足以支撑抗争意志的精神支点,以至于在公共话语领域,屡屡上演滑稽可笑的一幕幕而浑然不觉。
当下的公知一代,是意志垮掉的一代。这更是一个关乎群体心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有关学理与利益的问题。在韩乾看来,这样的一个群体身份,不但注定是政治抗争的局外人,而且极可能会被前进的历史所遗忘。不过,既然公知们不能实质地解决问题,那么随着时代的继续推进,公知问题,也许就这样顺其而然地退出历史,从而自行消解,如此看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