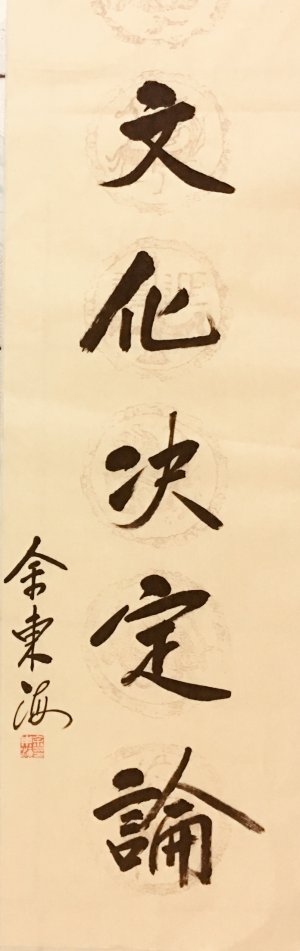
礼是文与质的统一。文指礼仪形式,各种礼仪形式和制度规范,都属于文;质指精神实质,礼的精神实质是忠信诚敬。孔子说:“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质胜于文,表现不够文明,形式不足;文胜于质,精神不够充实,实质不足。
等而下之的是有质无文和有文无质。有质无文,不学无术,或者形式错误,礼仪僭越,形式非礼。孔子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此即批评形式非礼。有文无质,不诚不敬,形式主义,是实质非礼。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即批评实质非礼。
孟子说:“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尽心篇》)这一章对实质非礼的批评最为深刻,针对的是当时的诸侯。他们对待贤者缺乏真诚恭敬之心,或食而弗爱,或爱而不敬,或恭而无实。
礼主敬。敬是礼的内核,礼是敬的表现。没有敬爱,只有礼物和礼仪,徒具形式而已。恭敬必须真实,在送礼之前就该具备于心。君子不会被虚假的礼仪所笼络。虚拘,以虚假的礼仪笼络人。朱熹注:“此言当时诸侯之待贤者,特以币帛为恭敬,而无其实也。拘,留也。”(《孟子集注》)
“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此言应是有感而发。例如,齐宣王对孟子就颇为恭敬和礼遇。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王任之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
孟子准备离开齐国的时候,淳于髡说孟子:“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告子下》)可见孟子在齐国虽无实权,但有相当地位。
崔述《孟子事实录》说:“孟子之在齐,乃客卿也,与居官任职者不同。”孟子准备离开齐国,齐宣王又表示:“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对孟子不可谓不恭敬。
但齐王“恭敬而无实”。孟子对齐宣王进言颇多,都不见用。所以孟子尽管依依不舍,最后还是选择离开。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篇》)孝养父母需要恭敬,与人交往也需要恭敬。食而弗爱和爱而不敬,即使食而养之或送上礼物,也仿佛将人当作犬马看待。
形式非礼易辨,实质非礼难辨。例如,孔子和左丘明都引以为耻的巧言令色足恭,很容易得到一般人的赞许。殊不知,非真实之巧言,非真诚之令色,非真敬之足恭,皆有其形而无其实,有其仪而无其义,表面工夫,不足道也。
百余年来学界流行一种非常非礼的恶习:在思想争鸣时,或妄测对方动机,或故意歪曲、恶意引申对方观点,或动辄将理义批评上升为针对性的道德批判乃至人身攻击。无论形式如何,都属实质非礼。如此对待师长前辈,尤为非礼。当然,非恶意的思想误读、观点引申和道德批评不在此例。
形式非礼和实质非礼,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形式非礼,纵有实质,非常有限;实质非礼,徒有形式,必不能久。
比有质无文和有文无质更等而下之的是无质无文。这是双重无礼,轻则夷狄化,重则非人化。百年来,不仅一般民众,三界精英亦普遍非礼,内则丧失了忠信诚敬的精神,外则态度恭高我慢、言语粗俗鄙陋、行为暴戾恣睢,此即双重非礼。我说过,五四至今是中国最无道、最缺德、最愚昧也最非礼的时期。
形式与实质统一,文质彬彬,内外兼美,唯君子能之。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非一般士人所能及也,即使君子,也可能有质胜于文或文胜于质的时候。故君子标准只可用来自我责备,不宜以此衡量、苛责他人。
某些无礼比较轻微,或不妨提醒,但不必苛责。例如,礼记曰,事亲有隐无犯,事君有犯无隐,事师无犯无隐。现代人很难做到。现代社会常态是,事亲有犯无隐,事上有隐无犯,事师或犯或隐。只要性质非严重,为人父母、上司和老师者,还是多多体谅为宜。
另复须知,教育领域的礼有其特殊性。某些时候貌似无礼,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启蒙方法。孟子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释尊的置答,老子的不言,禅宗的棒喝,都是特殊教育法。
孔子不见孺悲,就是一种不教之教。《论语义疏》引李充注:“今不见孺悲者何?明非崇道归圣,发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舛写之心,则非教之所崇,言之所喻。将欲化之,未若不见也。”李充认为,孺悲还没有生起“崇道归圣”之志,孔子纵然教他,也无效果,不如以“不见”来启发之。
202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