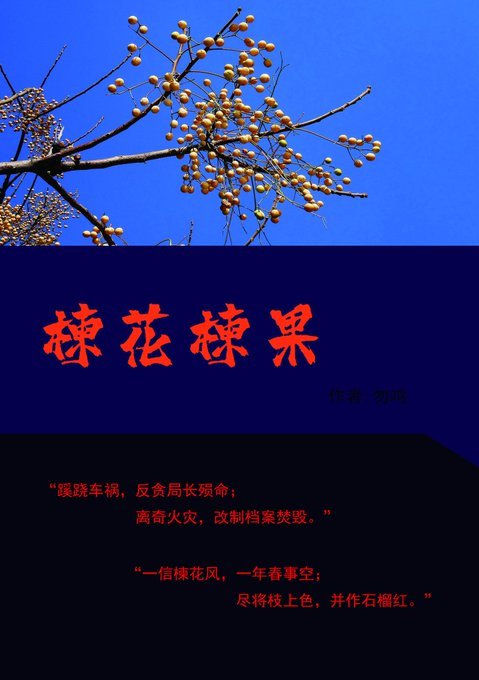
十
猴哥是号里的“内务部长”,负责管理号里的烟火、放茅、洗澡和分发饭菜。号里是不能抽烟的,要抽只能到风圈里去偷偷地抽,这些事情管教是知道的,但他假装不知道。风圈一天只开两次,上午一次和下午一次,每到这个时候,号里的瘾君子们涎着脸跟在猴哥的屁股后面挤出了风圈,眼睛都盯着猴哥手上的烟盒,猴哥会从烟盒中抽出几根香烟,交给号里几个“来钱多”、“资历老”和干活多的,并帮他们点燃,这几个得到了香烟的赶快走到风圈的四个角上,于是风圈里的人又分成了四堆,抽烟的正在吞云吐雾,半闭着眼作欲仙欲死状,看着的则瞪着眼睛,张着嘴巴,在焦急中等待。
每次有人犯被提审时,猴哥会对他说,在路上要多捡几个烟屁股回来。有些人犯在提审回来后非常高兴,说警官提审时给了他一只烟。
号里的香烟的来源有两个,一是人犯在会见律师时偷偷带进来的,二是自己的托送进来的,找彭管教做托,他每天都送,一天一包,从不间断。汪管教也要送,但不是每天都送。香烟是违禁品,火柴、打火机更是严重的违禁品,当托送进香烟、打火机和火柴时,会反复对老大说,这东西要收好,不能让武警查监时查到,每到武警查监,管教会提前来号里,拿走香烟、火机、火柴、指夹钳、针线等。
有时候因为查得紧,托不敢往里送,号里会断烟,这时猴哥开始想办法了,他会用拳头使劲地捶监室的墙,这是在给隔壁监室打电话,如果听到隔壁监室也在捶墙,这说明隔壁监室接到了电话,这时打电话和接电话的人都会跑到风圈里去,风圈的上方是封死了的铁栅,阳光可以进来,可以在这里晒太阳或晾晒衣被,可以同隔壁监室的人讲话。这时猴哥会问你们还有货吗?对方说不多了,猴哥会说我们断货了,想借点,对方说可以,但要算利息,不一会,风圈的上方就掉下了一包香烟,等号里有了香烟,会给隔壁号送去两包。
有时候查得紧,隔壁号里也断了货,瘾君子们坐立不安,这时候就得另想办法,对瘾君子们来讲,只要鼻子里能进点烟雾即可,于是猴哥找来纸和棉花,用纸把棉花包住,卷成一根根的,有了“香烟”,还需火,打火机和火柴早被管教收走了,于是有人找来了洗衣粉,均匀地撒在棉花上面,将棉花卷成筒状,放在鞋底的下面,在水泥地上使劲地摩擦,不一会鞋底下面的棉花就着火了。
猴哥的第二个工作是负责放茅,放茅也是看守所特定环境里的专用名词,就是大小便,所以放茅又分为放大茅和放小茅,小茅没有规定时间,而大茅一天只有一次,并且在统一的时间里挨个上。一个二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挤了二十多个人,如果不统一大便时间,那屋子里不臭气冲天才怪。猴哥就是负责放大茅的,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半是放大茅的时间,这时候他会喊一声,“放茅了!抓紧时间,每人两分钟”。他开始发放便纸,关系好的、对号里有贡献的、干活多的,他就发三节、四节纸,关系差的、刚进号的,他就发两节纸。对老大、老二,就让他们自己扯,不限量。时间也不限制在下午四点到五点半,他们随时可以上。
如为夏天,每天都需洗澡,洗澡时间与看电视时间重合。猴哥负责安排洗澡的次序和每组人数,决定给哪一组使用香皂、洗衣皂还是沐浴液洗发膏。冬天则一周洗一次。
吃饭是定量的,早饭每人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一小碟咸菜;午饭和晚饭每人两个馒头,一碗水煮的素菜。周五晚上改善生活,主食还是馒头,菜变成了红烧肉,每人一碗。
如果有钱还可订餐,早餐一份三十元:一个鸡蛋,两个肉饼,一杯牛奶,比外面贵五六倍。中晚餐每份五十元,一碗大米饭,两个炒菜。
经常负责打饭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另有几个是留所服刑人员,他们轮流充当中年妇女的帮手,其中有一个在13筒201室呆过,猴哥进来的早,认识他,如果遇上他打饭,猴哥会要他多给几个馒头,他一般会多给七八个。如果不是他打饭,猴哥也有办法——他让号里面年纪小、长得逗人喜欢、嘴巴甜的小孩打饭,当这个中年妇女走到监室门口时,小孩会不停地喊“阿姨好,阿姨多打点”,这“阿姨”心肠好,一般要多给五六个馒头。这多给的馒头分给谁,则是猴哥的权力了。号里面饭量大的要不饿肚子,只有拍猴哥的马屁。猴哥的托是彭管教,彭管教每天给猴哥送一包烟,号里面烟瘾大的要解决烟瘾问题,也得拍猴哥的马屁。因此猴哥在号里面的号召力比“雪村”强,只是“雪村”与许多管教的关系好,特别是与公安筒指导员的关系好,大家不敢得罪他。他们还听说,等“雪村”的二审下来后,看守所准备把他留在看守所管图书室。看守所的警官大都是中央党校函授班学员,都在等着他帮忙写作业写论文考文凭哩。
老大贾志富是一个村长,镇上征了他们村的地,土地补偿费被被镇上截留挪用了,他组织村民闹事,把公路给堵了,镇里的书记到他们村调解,他又让村民把书记绑了,要镇上拿钱赎人,后来来了大批公安和武警,把这事给摆平了,老大也抓进来了,他们村一共进来了八个人,怕他们串供,都关在不同的号子里。老大和汪管教是同一个村的,就让他当了老大。
刚进号子里的人大都心情沉重,只有 “屎壳郎”进来时乐哈哈的,“屎壳郎”原名史克平,这家伙涉嫌盗窃、强奸、拐卖妇女三个罪名,放谁身上都觉得沉重,可他高兴,认为里面管吃管住,有病还发药,又不干活,比家里还好。他家里穷,没钱上学,是个文盲,没钱娶媳妇,到了四十多还光棍一个,一天,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精神病人,介绍费二千元,他没钱,就偷了堂兄的一头牛卖了,把这个女精神病人娶回家来了,与她过了两三年的日子,这女的不生孩子,他后悔了,又把她卖给一个老头,收了老头一千五百元钱。
“那你们为什么不领结婚证?”“雪村”问他。
“领那干吗?我们村好多都没领。只有两口子在外打工,要住在一起的才领。我们又不出去打工。”
“办结婚证花不了多少钱的,就二十块钱。”“雪村”以为他怕花钱。
“我们那贵,要两百多。”
“没那么贵吧?”
“要给发证的包红包,一个包一百,两个就两百了,我们那里兴这个。”
有一件事“屎壳郎”一直没搞明白,想向“雪村”请教:“我偷了牛,这罪我得认,但老婆是我花钱买的,也在家里摆了酒席,这怎么就强奸了?还有,我买老婆花了二千,卖老婆只得了一千五,还赔了五百,本没收回,还亏了本,这怎么成了拐卖妇女了?想不通。”
“你与精神病人同居,精神病人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又没同她领结婚证,同她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
“但我们在家里摆了酒席的呀?那也不算数?”
“不算数。那个老头进来了吗?”
“哪个老头?”
“买你老婆的老头。”
“就是这老东西告的我,说我骗了他,他说我老婆是一个下不了蛋的鸡,要我退他钱,我不退,他就告了我。不过这老东西也没落一个好,”“屎壳郎”有些幸灾乐祸:“警察把他也抓进来了,同我一样,也是强奸。嘻嘻。”
“是的,同精神病人不领结婚证就睡觉,就是强奸。那偷牛的事也是那老头说的?”
“我自己说的,公安问我买老婆的钱从哪里来,我说钱不够就偷了堂兄的牛。”
“唉,唉,你说这干吗?你说自己攒的钱不就行了,干吗讲偷牛的事。那你干吗又承认收了老头的钱呢?”
“我的确收了他的钱呀。”
“他给你打收条没有?”
“没有。”
“你不承认不就得了?你承认收了钱,就承认了拐卖妇女的罪了。”“雪村”不想理他的事了。
“可我不会撒谎。” “屎壳郎”很委屈的样子。
这时候求医的时间到了,“屎壳郎”马上高兴起来了,他第一个排到了门口,
“这次又怎么啦?”医生问。
“牙痛。”
“牙痛是病吗?”
“不是。”
“不是病看什么病?把鞋子脱下来,用鞋底抽几下嘴巴就好了。”
“屎壳郎”在号里的一片笑声中悻悻的退了回来。“屎壳郎”自从进了号以后,不管有病没病,都要去找医生拿药。按规定,药必须当着医生的面服下,他也不管这药有没有毒副作用,每次都当面服下。他觉得这是好机会,他不能放过,他在外面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福利。医生是个好人,“屎壳郎”每次求医,问明症状后都给药,这次没给,可能是他看出了一些问题。这医生是红十字会的。
号子里本是个充满着悲伤、绝望、郁闷、沮丧的地方,里面的人都心事重重,空气在这里已变得死气沉沉,每个人都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只有“屎壳郎”除外,他的进来,给号里带来了不少的乐趣。
在规定的娱乐时间里,“屎壳郎”就成了大家娱乐的对象,号子里排了一个小品,名字叫《还偷了什么》。有人提议,现在开始表演小品吧,于是“屎壳郎”出场了,同时出场的还有猴哥,他扮演审案的警察,小偷由“屎壳郎”扮演。
“快说,你偷了什么?”
“我偷了一根麻绳。”
“麻绳上拴了什么?”
“一头牛。”
“牛拉着什么?”
“一架车”
“车上装的什么?”
“装了十头牛。”
“几头公牛?几头母牛?”
“我不认识公牛母牛。”
“不说?给我打”
于是上来一个人作打状。“屎壳郎”连连喊求饶。
……
“快说!你还偷了什么?”
“我偷了一列火车。”
“搁哪了?”
“搁我们家大衣柜里了。”
“快说!还偷了什么?”
“一架飞机。”
“搁哪了?”
“搁我们家冰箱里了。”
“快说!还偷了什么?”
“一艘航空母舰。” “屎壳郎”每次总是把“航空母舰”说成“韩国母鸡”,引得大家大笑。
“搁哪了?”
“搁我们家金鱼缸里了。”
“让你胡说,给我打!”
于是又开始打“屎壳郎”
“为什么要撒谎?”
“不说要挨打呀!”
“为什么胡说!”
“这不被您打糊涂了嘛。”
这时大家又大笑一场,这个时候,老大会露出一点点笑容,对猴哥说,开饭时多给他一个馒头。
“屎壳郎”整天高高兴兴的,只有一次让他有些伤心,那天他提审完回号,他对着值班民警喊道:“13筒201号在押人员史克平提审完毕,请求回号”,值班民警一直不理他,他又不敢自己回来,只让蹲在原地,重新喊一遍,值班民警还是不理他,他只好又喊,一连喊了二十多遍,一次比一次声音响亮。刚进号时“雪村”曾给他讲过规矩,说有些警官喜欢装怪,要多喊几次。他回号后伤心了好久——他已经把这里当成他的家了。
有一次,“屎壳郎”很认真地问“雪村”什么是冰箱,冰箱有多大,干什么用的。当他得知冰箱还没他们家的厨柜大时,恍然大悟,难怪他要挨打,冰箱里面怎么搁得下飞机?
一天上午,猴哥对姚古说,你都进来五天了,除了你老婆,也没人给你带东西,是不是还没找到托?我跟彭管教说说,让他给你当托。
姚古说那行。这时候,筒道里传来了脚步和叮叮当当的钥匙声,值班民警走到门口说:“姚古,提审。”
姚古走在民警的前面,根据民警的提示,出了筒道口,左拐进入巷道,沿着巷道前行,来到入监口。早有一个警官在门口等他。姚古在来的路上想,一定是小李警官和小方警官,到了才发现是一个细高个。
细高个将他带到一个审讯室,向他出示了警官证,坐下,指了指面前的圆木凳,要他也坐下。
“你是姚古?”
“是。”
“为什么进来的?”
“他们说我偷东西,”
“偷了吗?”
“没偷,我是冤枉的。”
“真没偷?”
“真没偷。”
“好的,以后有人提审你,你要这么说。”
姚古一时搞糊涂了。
细高个警官站起来,顺手甩给他两包精白沙:“记住,你什么也没偷。懂吗?过几天你就会出去,懂吗?”
“我懂。”姚古说。
“好的,你要懂,一定要懂。”
其实他什么都不懂。
姚古刚回监室,又听到门外在喊:“姚古,提审。”
这次提审他的是小李和小方。
中午,看守所财务室给姚古送来了一张存款单,金额为两千元,存款人是姚董。
姚古想,这姚董是谁?今天来看守所找他的只有李警官、方警官和那个不认识的细高个警官,是不是那个细高个警官存的钱?
姚董?姚古猛然想起了那个细高个的话:“你要懂,一定要懂。”他马上明白这钱一定是他存的,是要他懂事,不要乱说。
中午饭刚吃完,值班警官又在喊姚古提审,这次来提审他的是一个胖子警察,胖子将他带到审训室,审训室里早有一个秃子等在那,他说他是律师,你的案子很大,搞不好十年以上,他与公安这边关系很好,可以把这个案子压下来,先不立案,至于费用嘛,他伸出了一个指头。
“一万?”
律师摇了摇头。
“十万?”
律师点了点头。
姚古说我回去想想再说。姚古知道,有些律师和公安、检察官、法官都是勾结到一起的,为了让你多出点钱,故意把案子给您搞复杂,然后讹你钱后私分。他进来第二天“雪村”和猴哥都给他讲了的,说这几天可能有律师要主动找你,你可要全部推脱哟,就说家里穷没钱请律师,或者说已经请了律师。
姚古屁股把板还没坐热,值班民警又在喊姚古提审,又是一个警察在入监口等他,将他带到一个提训室,里面早有一个胖女人在等他,她告诉他是律师,
“我是你的朋友帮你请的律师。”说完递给他一张名片。
“我的朋友?”
“是的。”
“我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这个你就别管了。”
“那律师费用?”
“你的朋友出。”
“我的朋友出?”
“他还要我给你存点钱?”
“给我存钱?”
“他怕你在里面有受苦,给你存点钱订餐。”
“存多少?”
“一万。”说完将存单给了他
“啊。”他发现存款人又是姚董。
律师低声对姚古说,警察提审时要一概不承认偷了东西。离十五天还有十天,十天后我来接你出去,然后见你的朋友。说完给了他两包特制鹳雀楼香烟。姚古知道,这烟可不是一般的人能抽得起的,每包200多元,一支就十多块钱。
姚古回号将两包特制鹳雀楼香烟交给猴哥时,猴哥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了。他说这烟谁也别想抽,让老大拿去孝敬汪管教。
姚古将一万元的存款单交给了“雪村”,对“雪村”说,我们号订四份早餐和四份晚餐吧。老大、你、我、猴哥每人订一份。“雪村”觉得自己听错了,他一看存单,一万元,抬起头盯着姚古,好像不认识似的。他又看了看存单,的确是一万元。
这时候跑筒的过来说,有一个傻B在红十字会的护士发药时用言语挑逗女护士,把女护士气哭了,警官非常生气,这个傻B一会要来游筒,每个号都要准备一盆水,等他作完检讨后用水泼他的脸。
“我来吧!”猴哥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他打了一盆水,不一会听到脚镣拖地的声音,一个全身湿碌碌的小青年被两个人犯用铁链牵着来到了监室门口,可能是说话太多,他的嗓子嘶哑了,他用嘶哑的嗓子作检讨,并努力使声音大些,他的声音在颤抖,头发上滴着水,脸已被水冲得发白,眼睛是红肿的,监室内鸦雀无声,猴哥对着铁门把水泼了出去,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兴奋,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大家的心里都很沉重。
“全所三十多个筒,每个筒又有二十几个号,这小子惨了!” 脚镣拖地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雪村”第一个说话了。
“他的腿上还在流血。”猴哥的声音是低沉的。
“游完后还得关小号。”“雪村”说。
“雪村”到过小号,他是去照顾一个关小号的病得不轻的人犯,那小子是河北衡水人,在外面偷了一辆拖拉机,本来没多大事,可在外看病时乘机跑了,后来抓了回来,关在小号里,两个同去的警察不仅全年奖金、考评、晋级没了希望,还差点丢了工作,看守所也被全市通报批评,警官们把所有的冤气都发在这个逃跑的小伙子身上,把他打得半死不活后关了小号。这小号只有不到十平方米,为了防止人犯自杀,小号的墙壁四周贴了一层塑料泡沫。里面光线昏暗,一根两米长的铁链拴着人犯,铁链的另一头固定在屋子中间,如同猪圈里拴着一头猪,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拴着。
“雪村”说,打饭的大娘心肠好,每次打饭时都会给关小号的小子多打点,到了周五晚饭改善生活时,她会给这小子装上够他吃几天的红烧肉。
“那小子本来有病,又这么一折腾,三个月后就死了。”“雪村”每次提起他照顾过的那小子,心里都很沉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