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结束了地中海的“世界之海“”的荣耀,但工商业只是在地中海相对衰落,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新的海洋航线上的周边城市,且有了新一轮扩张。过有钱有势的好日子,本是人的天性。此种资本主义是不合罗马教庭统治理念的。过去它容忍意大利几个城邦国的发财致富,迫于圣战需要。但现在它的统治力已经衰落下去。因为它未曾消灭掉异教徒,反倒总是劳民伤财,不容忠诚不疲敞。这也是“文艺复兴”的由来。
十四、十五、十六三个世纪,是葡萄牙,西班牙,汉撒同盟、荷兰、英国角逐霸主的时代。此情景颇有点中国春秋战国之交,随着周室衰落,五霸争雄的故事再现。
争雄的必备手段是军力,军力的基础是经济实力,发展生产便当仁不让成了社会生活主要内容。
但直到十七世纪,这些霸主也就是个轮流坐庄罢了,形不成稳坐独超宝座达一个世纪以上的局面。说到底,是经济力制约了霸主的雄心。形象地说,若无特殊手段,牌桌上一定会是久赌无输赢。因为,若无革命性突破,传统生产的产量增加皆有个上限。再使用一个形象化譬喻:传统农耕条件下,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只要不违天时肯流汗,都能使一亩稻田产谷四五百斤。其中某人特能干加运气好亩产七百斤也做得到。但任你如何能干,亩产休想过八百斤。这便是上限。
那么,如果某人既能干又田多,凭一个规模效应也是可以压趴同行啊。
此说当然有道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仍用上例,首先田多总产量多,但投入的劳力也一定多,人和牲口的消耗跟着多。而没有几个国家想做就做得到。其次,单产高不等于群产高。再次,储存、转运的成本亦高。再再次,撞上天灾人祸,规模越大亏损越大……
从经济上讲,正是上限的存在,决定了历史上两大景观,一直演绎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
一,由规模效应形成的大国,任如何努力也只能存活几百年。这个几百年内,一般来讲真正的强盛时期不过两三代人。
二,要求得规模效应,和平开荒拓土与武力征服兼并便不可免。后者尤其一发便不可收,是因非和平方式的武力侵略,伴随的一定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仇恨从此埋下,化解仇恨谈何容易?
那么,何以中国存在了几千年?
实际,今人理解的“中国存在了几千年,”指的是文化传承了几千年,不是中国国体即政治中国或主权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从春秋到清亡,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本盘再加以延伸的这块华夏人栖息的广袤之地,不存在政治中国或主权中国,存在的是“天朝”、“四海”,以及刘姓汉朝、李姓唐朝、赵姓宋朝、朱姓明朝,爱新觉罗氏大清。此非拙文讨论内容,有一点是真实的,再强盛的“普天之下”都只存在了几百年,如前所述,其真正强盛时间也就两三代人。事实上,现代的主权不容私相授受的中国,只有一百多年。
再回到拙文主题。
十七世纪后英国经济一枝独秀,在此基础上打造了“日不落”帝国,功于它成功地突破了传统生产的上限。便是工业革命使生产力不再是算术级增加,而是几何级增加。而它推行的新制度,初期只是新生产力的润滑剂,渐成新生产力的制动器和保护层。
新制度的甜头激励了英国新权贵阶层的更大干劲,人也变得更加精明,便愿意付出接受权力制衡的小代价。然而,除了美国,法、德、俄还有尔后的日本,权贵们却只想得到甜头不肯付代价。具体地说,它们皆全力追求新生产力,对科学技术的重视首先是为了国而不是民,固然客观上扩大了人的视野促成了文明进步,却不懂得也不愿去探讨英、美新权贵的付出小代价,获得的是更大更久远的利益。随着机器生产带来的新生产力迎来了新的上限,商业市场也迎来了需要随份额大小而分配的瓶颈,由战争决胜负的旧把戏又上演了。
严格地说,二战的结局只是基本上遏制住了强国为开源而不惜打仗的冲动,功于这几点:1、战争代价太大,弄不好就得不偿失。2、核时代打造了恐怖平衡。3、随着民主国家增多,新制度、新观念起了相当作用。
但不要指望在争夺生存资料时人性善会压倒人性恶,从来社会学说济世功能有限。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的几率越来越小,愚意以为主要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的世界经济发展。这一波新生产力发端于半导体技术革命,步步深入,仍未止步于互联网。它不同于十九世纪前的工业流水线生产,抢占市场无需与侵占土地同步。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开战后前线与后方的界限不再很重要。
无疑,大国经济必要服从新的世界大势。
那么,红朝是怎么做的呢?
很大程度上,今日的中国二字是个抽象的虚词,红朝才是实体实词。谈经济便不免谈政治。
改开前红朝三十年,当然有经济,却无现代经济思想。因为完全从属于政治,而这个政治客气地讲,也是要回到中古时代去。这是一条通向死亡之路。改开后中国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前提是靠了世界的和平大环境。对越“自卫反击战”说重点是侵略,客气点说也有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幸的是适可而止了,未影响到经济大局。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此前三十年工农业生产皆处于“半休耕”状态,是几亿人手脚被紧紧捆绑的结果,由此出来了恢复性生产的莫大空间,也就是狗屁不通的“红利”吧。改开后相当时间内生产生活物质的匮乏,是有力的说明。可以肯定地说,今日若南北韩统一,金家王朝覆灭,北韩民生经济出来两位数增长指日可待。中国这个恢复性生产发展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便接近上限了。突出反映在朱镕基不得不对国企改制,打破铁饭碗,抓大放小。事态很显然,产量上去了,效益、质量却未上去,能耗惊人。农业怎么办呢?北京只能允许多余的劳力出外打工,做小生意,经济考量是次要的,目的是缓解社会矛盾。
朱镕基力促了中国经济入世,这既是一步远见卓识之棋,也是一步再无路可走之棋。他不会不明白,现代经济需要现代政治文化配套,但他既被中共绑架只能做到这样了。从长远看,他于中国经济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限于一代人时间看,说他救了中国经济也不为过。无论如何,入世使中国实现了从恢复性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突破瓶颈,带动商业进入了世界市场反过来又盘活了国内市场,商业作为经济酵母的作用从此凸现。但是酵母是经济水势,自身并构不成经济水流与水源,生产仍是基础。顺便说一句,马云曾批评北京的金融监管仍停留在“当铺”阶段,不过北京也有理由说金融乱象就是个《西游记》的盘丝洞。当然,猪八戒有权喜欢蜘蛛精的美色。
江、朱、胡、温二十年,经济上讲尽到了努力,绩效斐然。此种经济繁荣并非假象,于是此二十年内95%的中国人肯定经济改开亦非无依据。它理所当然让“先富起来的人”肯定改革开放。相应地,中共和邓小平得以一俊遮百丑,海外民运只能败阵,美欧情不自禁赞叹中国奇迹,国内的弱势阶层更加玩命般拼搏,因为生活肯定存在不公但仍存在机会,大小官媒纷纷口吐莲花……
但是此种经济繁荣并经不住大历史眼光的证伪。
概略地讲,此二十年的经济奇迹,史上不乏先例。最值得说道的是,从经济思想上看简直就是当年西班牙暴富时代的再现。
曾经的西班牙,靠着从美洲掳掠的巨量金银,一度在欧洲富得流油,钱多得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花。当然,富的是王室,是应该先富起来的强人,但小民多少也沾了光是事实。突出的例子是王室和社情容不下异教徒两百万摩尔人,把他们驱赶出去时,朝堂允许他们带走自身的财物。此非文明和人道,而是权贵们已不屑于那些小钱了。相当时间内,西班牙朝野毫不怀疑手里的金钱足以打趴欧洲与世界。
英国人却发展出了另一种经济思想:货币不万能,能够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更重要。有形的生产力比不上无形的生产力重要。无形的生产力只能建立在培植无形生产力的大环境基础上。
英西争雄,西班牙败,英国胜,从经济上讲就是个生产力后劲跟得上跟不上的问题。从此,此思想无从取代。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从常情常理上讲,中共权贵该明白上述道理了,该高度重视了。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中国还将面临新的经济瓶颈。
一,世界不再存在未发现未开发之地,新发展水平上的上限更难突破瓶颈了,传统的战争手段只会得不偿失。此情况意味着独超大国已是逆时而动,未来时代只能允许一强存在,各大经济体只能均衡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彻底打消走英、美独超之路的主意。
二,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只一个自然资源制约,人均财富占有量就只能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方向走。否则哪怕中国社会转型成功,世界也难答应十几亿人走拜金之路。而未来的中国不可能离得开世界,就必要处理好此关系。补救的办法只能是在社会公平、正义、文化繁荣、让身心舒畅上下功夫。事实上,今日中国离开了世界资源,经济铁定趴下。进一步说,且不去说数量不是质量了,即便中国“朋友”遍天下,高尖端领域的经济发展也非改开二字可以很快奏效的,历史欠账必要还。所谓的后发优势,弯道超车,用于粗放型经济可以,用于高尖端领域就多半是宣传需要。前者突出如房产、基建、高铁。后者则表现为华为,航天上的短板。
愚意以为,中共权贵中很多人不会不明白上述历史教训与未来走势,他们的问题是明白人重视不够,愚顽之徒偏不信邪。
例如,温家宝曾呼吁政改,指出不政改现有的成就也可能失去。他的见解肯定征求过胡锦涛的意见,他们的问题是有心无力加性格懦弱,由红二代权贵组成的董事会不答应。不排除某些个董事明事理,但人数少且也心存侥幸。此侥幸无非是情况尚不严重,尽可且行且看几十年。而多数董事确需时间,用于转移劫掠来的赃物和安排亲属退路。至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死硬派董事,利益不允许他们走“邪路”,只会讲党史唱红歌的脑瓜又不肯承认自己无知,加上拍马屁的人那样地多,脑瓜早就昏昏然,还说他们什么呢?当然根本问题是制度太反动,加上三十年的腐败、糜烂,一代人都不行了。大量的小粉红就不说了,那些个专家、教授、国师实在该给党国出几个高明主意。
但说这批人全无警觉也不公允,例如反贪、维稳、净网、一带一路等等,便是他们一方面争取时间,另一方面想打造奇迹的大动作。然而这是一厢情愿。无情的事态是时间拖得越久,官场越难治理,社会越发糜烂,经济越来越由实而虚,债务泡沫越来越大……事儿没完,特色稳定激活不出工匠精神与发明冲动尤其执着的基础研发,要占领新技术的新生产力制高地,便只能阴招损招偷与骗一齐上,于是与大金主美国闹翻。本来,倾销廉价产品终究有个顶与度,贸易上美中摊牌是个时间问题。如今时间提前,争取时间的盘算便落了空。怎么办呢?这帮二杆子便迁怒于一切不合口味的人事了,也就一个闹剧连着一个闹剧。
今日中国经济,政治的演进趋势日趋凶险,但非习当局所造成,祸根早已埋伏,习当局加速了它而已。
那么,换掉习当局,深化改开,中国经济、政治还有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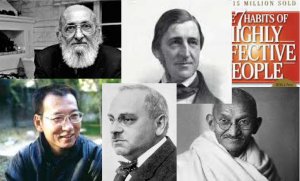 中国转型的当务之急首先在于政治,而非文化
中国转型的当务之急首先在于政治,而非文化笔者以为,再撑个三五年不是大问题,但从趋势上讲,晚了,一切都晚了。就与美西关系而言,习总上台就应撤除用于台海的导弹,履行一国两制承诺,贸易顺差上适当让步,关系并不至于闹僵,而此让步并不会妨碍中共统治。对内,继续胡温时的“不折腾”,允许小民骂骂娘,坚决不搞国进民退,停止土地财政,颁行阳光法案,放手媒体监管等等,切实体现改开有点干货,官场与社会便不至于腐败,糜烂不可收拾。如今,与美西的关系恶化于中共和中国仍不致命,用钱仍旧能大致摆平。以中国之大,韭菜之多,不怕榨不出油。从来瞎子见钱眼睁开,美西也是人组成。很多分析指时下中共的强硬言行,主要是做给国内看,窃以为很有道理。于中国致命的是:
- 不换掉中共官场大多数人,腐败暴政不能扭转,可是常态下此事想都不要想。传统的革命手段肯定不是办法,可惜和理非无非一厢情愿。
- 社会生活的国仍是国,民已不民,已表现为西风东渐以来从未有过的冷漠、装睡、弱智、犬儒、至害、绝望,等等,具备了不是王朝末世而是国家解体的一应条件。
- 现有的经济结构,经济关系面对中等收入陷阱几年前便已止步,官方的靓丽数字全不可信。今日的注重分配之说与还是蛋糕做大之说,皆属于说了也是白说。属于弱智权贵说给弱智草民听的春秋梦话。
- 某种意义上民主、人权、宪政短时间内不但不能奏效,而且会加剧上述三点的剧痛,病入膏肓的国体、政体、文化已失去了承受力。笔者甚至有点儿体谅中南海为什么强调正能量了,问题是得有正能量啊。因为中共尽可以自封伟光正,但中共总不能把赖小民说成焦裕禄吧。而赖小民何其多也,他不该在蛆堆里太摆谱。这是典型的报应。
规模的效应从来是特定时空内巨大的惯性力下仍能表现的不可一世,致命伤是雪崩发生便无任何力量阻止得了它。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中共吹嘘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何尝不是把所有的鸡蛋放一个篮子里。篮子平安,皆大欢喜,篮子打烂,怎么办呢?
结语
作为中国人,感情上当然希望国泰民安,各方面走在世界前面,但感情不能取代现实。展望本世纪,经济上中国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便是了不得了。
此目标并不宏伟,但实现此目标仍何其艰难。
- 尽快终结中共变态统治,改行民主、人权、宪政为当务之急。因为民主、人权、宪政未必就能解决技术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撒旦的问题,没有民主、人权、宪政便想不都要想。武汉病毒已是预告。
- 政体充斥罪恶,国体也存重大缺陷。四世同堂大家庭模式必要让位于小家庭生活方式。国家只有切实尊重人权才是个不孬组织。
- 经济的出路仍旧不外乎生产资料上开源节流。节流不易做到,开源更难。参照发达国家经验,非两代人含辛茹苦不能奏效。毫无疑问,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只能是新材料,新能源,太空经济。这就不只是一个反对暴政的问题了,还需要朝野切实改变思维。
- 所以文化必应跟进,津津乐道于悠久历史已是没有出息的表现。国学可以没有,世界学不能没有。文明的生命力主要在未来。这是一条非走不可之路。
愚意以为,如果十年之内做不到第一点,三十年之内做不到第四点,尔后则有关中国的所有话题都意义不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