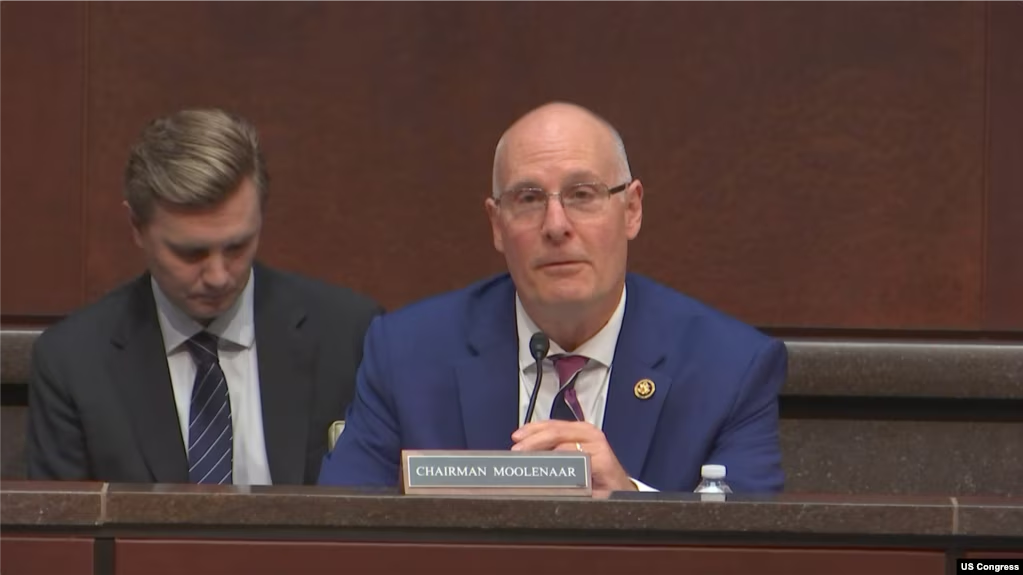|
7、啊——“同志”
一
1957年5月,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复阐明提倡,苏洵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白居易从古人之语中提炼而成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样的一些名言,日益深入人心。每天翻开各种报纸,几乎整版整版,都是各界人士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报道。尽管有些批评十分尖锐且不尽妥善,但提倡大家畅所欲言并公诸报端这举动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党的领导胸怀广阔、大度雍容,何况很多意见是中肯可行的,虽然乍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
这当儿,为了节省时间,我和新华社的少数不愿每天坐班车来回跑的同志,已住进了外交学院干部学员的宿舍,本人还被选为中央很多部门派到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一、二、三四班住校同志的党支部书记。尽管自己的肚子里已积存了多如乱麻的意见,但我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没写过一篇墙报稿。
我总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没有明确具体地宣布党内同志如何参加整风鸣放时,自己应该在公开场合下谨言慎行。
其间,惟一正式表过态的,只有这么一件事——整风伊始,许多省市的负责人为了表示自己与人民同甘共苦,决心清扫官僚污垢,装模作样地打扫一小块街道,或浮皮潦草地下厂下乡走走看看,我们的报纸电台便颂扬备至。我认为这做得太过分,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把戏,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1957年5月18日的新华社内部刊物《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它只有1 300来字,下面就是它的全文:
瓜不熟不甜
自从中央决定整风以来,全国各地有许多高级干部开始参加体力劳动,这是好事情;但是,在某些稿件中,出现了为时过早的赞扬,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若干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在思想上、生活上、作风上,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人们在过去不敢这样明说。现在刚刚开始转变,有些人拿起扫帚、铁锹也不过几个小时,我们马上就为他们大书特书,说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群众是如何地感动,等等,这未免说得太早了。也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经我们这样一宣传,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人原是些天生的不该劳动的人,因而才惹得群众惊异和感动。有的消息中特意加上群众的反映说:“在旧社会里,从未见过市长扫街。”然而,在新社会建立以来的八年中,这种现象又何曾有过呢?我们的这种说法怎能说服人呢?
在战争年代里,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是所有革命者的传统精神。今天只是开始恢复这种精神而已,并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新鲜事。事实本身就能向群众揭示出事情的本质,用不着我们去添枝加对、抹脂搽粉。特别重要的是,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如果在这阵风过去之后,一切归复如旧的话,我们怎样向人民交待呢?怎么对得起广大的劳动人民呢?他们年复一年地辛勤忙碌,使我们饱食暖衣,几乎一直默默无闻;而我们的干部在一生中只扫了一小段街道,挖了两个小泥坑坑,反而一举闻名于天下,真是太不公平了。
这种做法是老病复发。我们如果敢于面对事实,那我们就会明确地认识到:片面、夸大、过分的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是在我们新华社甚至是全国新闻界多年来的致命癌。我们只要得到中央的一句话,不顾事实如何,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阵风,而且风势越猛越好。可是到头来,事实并不完全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美好,有的甚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使得广大群众怨声载道,消极失望。
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该说就说,该怎样说就怎样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古话说得好:“不为有利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的,而不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说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只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过去战争期间,人民之所以能够推心置腹、相信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斗争在一起。我们要说的就是他们想说的,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说胜利就有胜利,说有困难就是有困难。因而他们在胜利时不骄傲,在困难中不气馁,一切的一切都早已心中有数。
可是在进城之后,我们和他们疏远了,却和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合为一家。我们几乎只能照“章”办事,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真话,说了不少的空话,也有意无意地说了一些假话。尽管我们的用心是同样的善良,但在若干问题上,人民说我们欺骗了他们,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痛苦地深思么?
二
6月8日,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声威赫赫的“反右斗争”,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顷刻之间,那些被报纸以欢迎的姿态发表过言论的人们,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陈其尤、陈铭枢、陈达、钱孙卿、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费孝通、冯友兰、向达、谢雪红、许德珩、黄琪翔、黄绍竑、黄药眠、葛佩倚、林汉达、刘王立明、陆侃如、陆诒、龙云、潘光旦、彭文应、沈志远、孙大雨、谭惕吾、陶孟和、曾昭伦、王造时、叶笃义、沙文汉、艾青、丁玲、陈企霞、陈模、陈沂、江丰、秦兆阳、钟惦棐、冯雪峰、徐懋庸、李世农、邵燕祥、刘绍棠、彭子冈、曾彦修、王翰、王若望、吴祖光、徐铸成、肖乾、顾执中、浦熙修、谭天荣,等等等等的党内外人士或青年学生,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被说成是封建、官僚阶级的残渣余孽。
许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复保证“广开言路”,欢迎一切人帮助我们党纯正党风的么,怎么突然自食前言、反目为仇呢?
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去,听取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做报告。由于我是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同志所组成的党支部的书记,我也去听了彭真的报告。
彭真精力充沛,红光满面,音宏气足。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也说到了龙云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觉察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一方面,党内也的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这更需要予以无情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
“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这也需要大家协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与完善之。
“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这时,彭真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彭真热诚坦率,语重心长,侃侃而谈了两个多小时,尤其是后半部分的讲话,说得我们的心头都热乎乎的。一切茫然与疑虑,都随着大家长时间的掌声烟消云散。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预期效果,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当天晚上,中央许多部门住外交学院学员的英、法、西班牙文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就在宿舍楼洗漱室隔壁堆杂物的屋子里,举行了联席鸣放座谈会。
我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任其发展,必将国闭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对其抑制与消除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话,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举国上下都应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减过分优厚的福利拨款,以大力缩小国家干部与工、农、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悬殊。同时改变统购统销中某些过死过急的做法,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精简高等院校的政治课,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专业,等等。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大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泥”的劲头。
不日,新华社又召集所有学外文的同志,不论住在社内还是住在外交学院的,在“口”字楼顶的那间大会议室里开鸣放座谈会,我又照样讲了一遍。
在全国一片“反击右派”声中还说这样的一些话,岂不自作鱼肉送刀俎?
不,我不这样认为。就是没有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与保证,我也要这样讲。
小时候读私塾,恩师姚荫卿老先生,常常在我的书法练习本的空行中,出些上联让我对,偶尔也写点富有哲理的词句让我背。有一次,他写出了这么两句话,“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我一直牢记未忘。当我对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时,就如骨鲠在喉,非吐不可,并在私下早就对一些同志明白表示过,即便有人可能仿用斯大林的错误手段来对待敢讲真话的同志,我也要说出别人可能不敢说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报告和保证,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指示,是一大“阳谋”,我们的许多同志竟被“谋”上了!
当我从外交学院被召回新华社接受“帮助”的时候,同志们在“口”字楼顶的大会议室里,用小稿纸写的批评我言论的每一份小字报上,都还口口声声称我为“同志”,而《人民日报》总编辑与新华社社长一身二任的吴冷西,就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责骂我的大字报。我的妻子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要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判。
我不服,主动拿出了连我的妻子都不知道的那封给毛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的还没写完的长信,以昭心迹。谁料到这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求之不得的人称做“万言书”。他们指令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我总攻击的“炮弹”……
8、欲加之罪
一
1957年7月25日,新华社在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中,点了我的名。8月7日,新华社又专门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发了一条长达3000多字的新闻,竭尽胡诌编织之能事。其全文如下-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新华社北京7日电」新华通讯社总社最近以来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会和大会,揭露和驳斥党内右派分子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
戴煌是新华社记者,在194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他就对党不满,反对党,以致企图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来推翻中国共产党。戴煌曾说,如果共产党再不改正“错误”的话,他就要组织新党。他说,这个新党的名字没有定,叫“新共产党”,或者叫“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或者叫“第三党”。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新党的纲领、目的就是要“消除干部和人民之间的生活剪刀差”、“实现民主自由”和“消灭特权阶级”。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诬称。
戴煌利用记者工作上的便利,到处搜集攻击党的“材料”,随时随地进行造谣诬蔑。他的狂妄的反党言行是一系列的,它涉及到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国际问题以及人民新闻事业等各个方面。
去年11月,戴煌就开始写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书”(此信还未写完),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他在“万言书”中谈到“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的问题时肯定地说,“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按照戴煌的荒谬的说法,这个“特权阶级”已经成了一个非要打倒不可的“剥削阶级”了,他硬说这个所谓“阶级”同人民之间有着“生活的剪刀差”。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谬论,他竟无耻地捏造了这样的“事实”:“除大米之外,占人口5%的革命者的消费量一定会比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消费量要多得多!”他恶意地煽动说:“猪肉和食油都让共产党员和干部们吃掉了。”他叫喊:“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老百姓已经“悲痛地失望了”。甚至,他竟这样叫嚣说:“旧的统治阶级被打倒了,新的统治阶级又站起来,再发展下去和台湾合并算了!”戴煌在“万言书”中还用他去年回家(他的家在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搜集的一个违法乱纪的干部的材料,作为攻击党的“最有力”的炮弹。他把这个干部的材料加以渲染夸大,他说:“今天的人民和我们的党距离得多么远!”“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这种黑暗的深渊!”戴煌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他说,“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的官僚习气。”他说,他原先“只以为中央是清醒的,会为人民迅速办事的,谁知道也是同样的官僚,官僚!”他竟狂妄地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应该出来检讨。他甚至恶毒地攻击中共中央说,“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他狂妄地要中共中央“老老实实”,“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
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仍然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党和国家进行恶毒的攻击。在6月13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向党放出了一支最恶毒的箭,他说,他对国家的意见,“用五个大字来概括-神化和特权-这就是国家矛盾的根源。”这五个大字,就是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的基础。
戴煌诬蔑说,自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认为“自己高于一切”,“把自己神化了”。他对党和国家的干部极尽诽谤之能事,他说今天的干部是“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他企图把全国的干部一棍子打死,硬说,“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除杀人放火外,无恶不作”。他强调这一切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他狂妄地攻击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他对毛主席是“早就怀疑的”,说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就“开始怀疑毛主席犯错误”。
在大家的揭露下,戴煌承认他“诬蔑党的\’神化和特权\’的说法,不是随便说的,而是久经考虑的”。当同志们质问他为什么到处散布反动言论时,他说,他“要唤起群众,目的是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对党施加压力,以改变现状”。戴煌所说的“改变现状”,就是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所承认的要组织“第三党”,取消共产党的狂妄企图。
不仅如此,戴煌还不惜从各个方面来诋毁新中国。他甚至把今天我们国家伟大的建设事业也看成是“今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他认为,建造武汉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那也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值得“自豪”的。
同时,戴煌还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来诋毁苏联。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戴煌反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他说,苏联的出兵,“从公正及道义上”来说,“是讲不过去的”。他并且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地说:“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戴煌对党的新闻事业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他强烈地要求取消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向党要求新闻事业的“独立性”。他诬蔑人民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他更到处恶毒攻击新华社的领导人,他的目的是撤掉这批领导人,拆掉新华社。去年9月,有人控告他在家乡私自召集地主、富农、被斗家属开会,搜集村干部的材料,煽动群众斗争村干部。为了查明真相,新华社派人到他的家乡进行调查。戴煌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恨,他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控告新华社采取“秘密警察手段”,对他实行“政治迫害”。
戴煌还同社会上其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他认为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员的说法“有其道理”,他同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的“党天下”等谬论。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说:“党内\’三害\’的危害性远远超过右派,为什么现在不反\’三害\’却反右派?”
戴煌口口声声说他是“人民的喉舌”。他说,他对浪费国家财产、挥霍人民血汗的人“恨之入骨”。可是,根据大家的揭露,他恰恰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伪君子。他一贯地追求个人名誉地位。去年,戴煌领了1200元稿费,一个钱也没有交党费,自己大肆挥霍,大吃大喝。在国家和党号召认购建设公债时,他只认购40元。他在做驻越南记者回国时,曾经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去年他为不给他提级,内心极为不满。
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对于戴煌这种种反动言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指出,戴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由于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和打着新华社记者的幌子,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大家还揭露,戴煌老早就站在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立场上。从解放后一进入城市,他就开始犯错误,后来在国内和国外做记者工作期间,又屡犯错误,党曾不断地给予教育和批评,希望他认识和改正错误。可是,戴煌不接受这些教育,相反他对党深怀不满,对于屡次所犯的错误,或者当面抗拒,或者假检讨而后推翻,然后更加猖狂地攻击党。
从去年起,戴煌就更加露骨地处处同党对抗,处处钻空子,他甚至说,“领导就是官僚主义”,“所有反领导的人,都是好人”,他表示要同他所说的“官僚特权集团”斗争到底。他并且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宣布,他要“准备受打击”,“准备坐牢”。这种种情况,都说明了戴煌走上反党的道路绝不是偶然的。同时经过几次会议的揭发,在大量事实面前,戴煌还承认在他的周围有一个“小圈子”,进行了一些反对领导反对党的活动。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们认为,戴煌是记者群中的害群之马,他们一致表示要决心继续揭露和批判他的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要他彻底缴械投降。
二
不难看出,这条新闻的主要内容,几乎都是从我那被称之为“万言书”的尚未写完的长信及日常言谈中摘出的片言只句,而且对我的人格也进行了污蔑诽谤。
不说别的,单说“戴煌领了1200元稿费,一个钱也没有交党费”等等来说,就完全不是事实。这笔稿费,我确实是拿过的。但是稿费一到手,我就遵照党的“额外收入缴纳党费5%”的规定,如数缴纳了党费。我所以没能超额缴纳,是因为上有老母需要奉养,一个没有分文收入而又害有肺病的姐姐需要我的接济,一个哥哥因子女众多欠了国家银行的贷款需要我帮助偿还,另有几个读中学的侄儿需要我帮助他们交纳学费和伙食费,我哪有能力购买过多的建设公债和超额缴纳党费?
所谓“自己大肆挥霍,大吃大喝”,也不过是给自己的妻子做了一套衣服,花去了几十元;身边的同志说“拿了稿费要请客”,请他们到西单商场内的峨眉酒家吃了一顿晚饭,连酒水在内也只花了十元左右。
所谓“在做驻越南记者回国时,曾经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这是似是而非的谣言。事实上,当时决定我回国休假,我的行装和日常用品都还放在河内,由于妻子刚生了孩子,苏北老家又急需用钱,才预领了休假两月的工资,休假结束后,才决定我不再去河内,这怎么能说成是“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呢?
至于“去年他为不给他提级,内心极为不满”,这更是没有影儿的事。事实上, 1956年秋天国家为大家普遍调级时,我刚进外交学院学习。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脱产学习的人员,一般均不在这次提级之列。可是,在我根本不知情的背景下,新华社主动给我提了一级,我还有些莫名其妙,何来的所谓“内心极为不满”?!
对所有这类问题,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在“批判揭发”我的大会小会上,我都曾反反复复地作过完整的阐述与说明。但是擅长于胡诌的高手们仍要如此活灵活现地予以编造与歪曲,以混淆视听。
这就是一些“‘老战友’与‘老同志’”!
三
这条新闻,尽管如此地背离事实真相,但既然由新华社公开播发了,第二天的全国各大报都普遍照用不误,并随心所欲地标出了“各有千秋”的大标题-《人民日报》:《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来围剿戴煌》;上海《文汇报》:《戴煌想干什么?》…………
香港的一家别有用心的报纸在其头版头条,刊出火柴盒大小的九个大字:“新华社记者也反中共!”台湾方面,则以台北新闻界名义向我发布了公开信:“欢迎戴煌先生到台湾来。”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漆德卫,在其《北京反“右派”的浪潮》的新闻中,前半段说的是丁玲与“丁陈反党集团”,后半段就写到了我这个被他称做的“新华社的年轻工作人员”。
法新社驻香港记者洛甘,当天就摘转了新华社的这篇稿件,说“新华社指出这个共产党员记者自从1944年起就是一个反党分子”,“人们揭露戴煌曾经着手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万言书,在其中攻击共产党领袖,指责党的干部对群众采取狂妄和傲慢的态度。戴煌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发动他的进攻的。”等等。
紧接着,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解放军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新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它的全文如下——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本报讯 新华通讯社揭露出解放军分社一个以戴煌和李耐因为首的反党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另外两个成员是韩庆祥、路云。他们四个人都是解放军分社记者,大尉衔派遣军官。在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12日举行的最后一次斗争大会上,戴煌、李耐因等已经被迫低头认罪。
戴、李反党右派小集团的全部成员都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野心家,他们从1955年以来,长期地怀着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对党不满的情绪,经常地背着党和组织纠合在一起,谩骂和诬蔑新华社的许多领导同志,打击排斥别的军事记者,进而对党的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政治制度。新闻事业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共鸣”了许多反动言论。右派分子戴煌就是根据这些反动言论写了一部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书”,他并且还在小集团中酝酿过要组织“第三党”、对共产党进行斗争的狂妄企图。
戴、李小集团诬蔑我们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是“新贵族”、“特权阶级”,并且荒谬地说这是“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决定意识”。他们歪曲党的集中领导制度“必然会产生个人崇拜”。由于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假民主很欣赏,因而大肆攻击我国的选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他们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一道高唱“今不上。昔”“中不如外”的反动论调,来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荒谬地说像长江大桥和飞机制造厂等伟大工程“也不过是世界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戴煌、李耐因等大多出身于地主阶级和深受剥削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眼中的我国农村也是“黑暗和痛苦的深渊”,因此狂喊“农民太苦了!”“共产党忘本了!”等等。同时,他们还诽谤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比不上解放以前”,文学艺术不如“五四”时代,电影艺术多半是“公式化”,新闻事业是“教条”,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我们伟大邻邦苏联的许多诽谤,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的叫嚣一模一样。
戴、李小集团还曾经处心积虑地阴谋篡夺解放军分社的领导权,妄图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新闻观点强加于党,变解放军分社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在这一重大的阴谋活动中,戴煌、李耐因分别以小集团的“统帅”或“军师”身份,指挥、率领着“急先锋”韩庆祥和“大将”路云一道,向党发动了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猖狂进攻。
戴、李小集团选择了去年春天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的时机,发出这一进攻的信号。他们在这次会议中利用当时军事记者们的某些不健康的情绪,并且蓄意捏造了许多谎言,煽动军事记者在会议上“诉苦”,借此对新华社领导进行恶毒攻击。
当新华社为了加强军事报道和便于培养军事记者,决定集中新华社海防前线分社、志愿军分社和国内部军事新闻编辑组的全部军事记者成立解放军分社,而解放军总政治部对这一措施也表示完全赞同时,戴煌、李耐因等开始反对,继而认为此事大有可为,便密谋出一套同总政、新华总社的领导意图相对抗的“方案”。他们借口“把军事报道提高到国际斗争水平”、“准备应付战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根本否定和平建设时期的军事报道,并主张除了“只留几个人看门”以外,调大多数军事记者去学习外文等技术知识,学习回来只写自己愿意写的任何东西,所谓“自由发展”。此外,他们并且坚决反对解放军分社接受总政的领导。这个“方案”实质上是戴、李小集团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政治方向的纲领。当总政和总社不同意这个“方案”,提出解放军分社“以工作为主,照顾学习”的方案时,戴、李小集团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接着,李耐因和戴煌又密谋出另一个“解放军分社归总政建制,同时保留新华社军事组”的“方案”来,企图把军事组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与总政领导的解放军分社分庭抗礼。他们还狂妄地在小集团中对这个“军事组”的方针、编制、人选等都作了具体安排,密谋抬出李耐因当“军事组”组长。可是他们的这个阴谋在领导和其他军事记者的坚决反对下又告破产了。
从此,自称“把握情势,制定决策,划分阶段,指挥斗争”的李耐因,便迁怒于受总社领导上委托负责筹建解放军分社的同志,而要戴煌、韩庆祥、路云出面,四处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并且还威胁总社领导说:要“联名抗议”,“集体罢工”!李耐因并亲自赶往福建前线搜集材料,企图骗取驻福建前线的军事记者的支持。小集团还背地策划、积极活动夺取采编主任职位,以便控制解放军分社。甚至捏造“群众要联名向中宣部控告”,公然诬蔑新华社领导同志。
在解放军分社成立后的一年来,李耐因和韩庆祥共同采取对工作消极对抗的态度,在军事记者中挑拨是非,制造不和,并向总政宣传部新闻处、解放军报以及首都各报社和广播电台的派遣军官,大肆散布攻击解放军分社领导同志的谰言。他们还采取了许多极为阴险卑鄙的手段,破坏“八一”三十周年的报道,企图借此把解放军分社的领导同志打下台,把解放军分社搞垮。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们一致认为,戴煌、李耐因反党右派小集团长期以来早已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一年多来对党的疯狂进攻,实质上是一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新华社从7月中旬开始发动对右派分子戴煌的斗争以及继而揭发出小集团的内幕以来,到本月12日为止,先后举行过三十多次大会和小会,终于迫使这群右派分子不得不在大量的事实和真理面前低头认罪。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
看了《解放军报》在头版刊登的这篇报道,可谓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们的又一“杰作”。至此存照,使人们一窥那个时代这些“高手”们歪曲捏造、致人于死地的毒辣手段。
事实真相是,我与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同志都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开始都从事新华社军事报道,在横渡长江后或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曾一道工作,调总社后又在同一个部门,自然熟悉亲近些。没想到这就成为一条罪状-“为什么你们来往多?这还不是\’小圈子\’、\’小集团\’?”先定“罪”,后“求证”,一个“反党的”、“有阴谋”的“右派小集团”就这样下了定论。
因为定为“反党的”、“有阴谋的”、“篡夺领导权”的“右派小集团”,于是正常的出差去作报道工作,也成为“阴谋活动”;正常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成为“互相呼应”;连日常的闲聊天,也成为“背着党”的“小集团活动”,那“目的”据说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原先的军事组和后来的解放军分社充其量不到十个人,而把这个“小集团”竟描绘成有“统帅”、有“军师”、有“大将”、有“急先锋”、有“纲领”,还有什么“把握情势,制定决策,划分阶段,指挥斗争”的一套“战略战术”,不啻是一场夺取国家政权的“宫廷政变”,这岂非咄咄怪事! 真是可悲又可笑!
四
随之,江苏省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戴青天”还乡记》,把我家乡的那个最坏的新恶霸描绘成了一个大好人。似乎我既然成了“敌人”,那么“敌人”所反对的,当然就是“好人”了。
新华社机关报《前进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亲者痛,仇者快》,把新华社的那条电讯在国内外引起的一切恶果的责任,全部推在我的身上。
霎时,我硬是被一些人推进了万丈深渊,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
不仅如此,凡是平时与我比较谈得来的同志,不是“反党右派小集团成员”,就是“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几乎无一幸免。根本不是什么“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而纯粹是徇私报复,落井下石,搞臭骂臭,浊流横溢。
这样的所谓“批判斗争”,对我整整进行了三个月。
不过在这里我应该说一句公平话:虽然对我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斗争”,在语气文字上对我进行了许多恶意的诬蔑诽谤,但在行动上并未损害我的人身尊严。
当时,正处于闷热的夏天。我忙于记录别人的批判发言和所提的问题,紧张得汗流泱背,社党委书记普金在一旁给我扇扇子,社党委委员了九递毛巾擦汗并倒来了茶水。这些文明举动,非“文化大革命”中的拳打脚踢“造反有理”可以同日而语的。
后来,也许全社接踵而出的“右派分子”太多了,连一位汽车司机和一个未满 18岁的电台练习生也被“揪”出来了,实在“批”不过来了,才草草结束了对我的“批判”,叫我写“检讨交代,提高认识”,同时“必须认真学习康生同志选定的九部马列着作,争取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此刻,我内心斗争之猛烈,犹似江海汹涛之激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