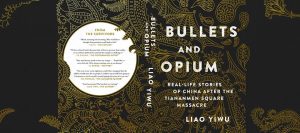
有两件事促使我对此书进行全面修订,内容比初版调整了许多。 一是2017年3月30日,余志坚突然去世,之前数日,我们曾有过越洋电话; 一是7月13日,刘晓波被谋杀在严密监控中,随后被官方海葬。 这是天安门大屠杀前后的两名主要见证人。 刘晓波也是此书最早的读者和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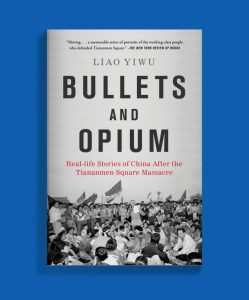
自2005年初夏算起,此书历经12年,那时晓波第三次出狱已近6年。 他总是被软禁,从北京来成都找我,得有关部门特批和暗中保护。 他给我写了不少信,其中有两封很重要,一是关于长诗《大屠杀》,一是关于《证词》,却是借题发挥,倾泻他自己的心结。 可以说,在17年前,他写信给我那一刻,就注定了眼下“以身殉道”的命运。
他是为此书敍述的人与事而死,他要与亡灵共舞,与受难者同在。 1999年一个冬夜,他出狱不久,我从成都去北京见面,一起到雍和宫附近的忙蜂酒吧。 他和忠忠不喝酒,我和刘霞,还有朦胧诗元老芒克喝。 我酒量差,醉得早。 邻座有几位诗人轮流上台朗读,芒克也朗诵了他的《没有时间的时间》,我吹箫伴奏。 刘霞笑着说老廖来一个。
 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出版的官方圖片新聞畫冊《暴徒的下場》。死於這場全城大搜捕的人數至今不詳。
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出版的官方圖片新聞畫冊《暴徒的下場》。死於這場全城大搜捕的人數至今不詳。我朗诵了《大屠杀》。 夜深人静,晓波突然哭得像个孩子。 我记得那一幕,他说老廖你,你,你,你在这种地方朗诵个鸡巴。 然后起身扭头走了。
当晚他写下这封信:
老廖:
你太折磨人了。 听你的声音使我怀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否充足。 泪水往心里流,但流过泪之后,生活依然在无耻与轻浮中照旧。 人都死了,只有狗崽子才能幸存! 我是狗崽子吗? 我们是狗崽子吗? 太怜憫自己了。 狗还他妈的有狗性,中国人有人性吗? 没有人性的人和有狗性的狗之间,造物主的恩典肯定给予后者。 我们连狗都不如,我们的子孙连狗崽子都不如。 中国人什么都不是。 鲜血不是什么,背叛不是什么,遣忘也不是什么。 因为这首《大屠杀》,你坐了四年牢,我以为值得。 牢狱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点良知。 你真不该与他们一起朗诵,你的世界早已属于另类,而他们则很正常、理性,这甚至包括xx。 耻辱地活着,为了无辜者的血,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理由。 “六月四日”的黎明,是我心中最黑也最红的日子,而六四之后的所有白天与夜晚,既不是黑也不是红。 如果无耻也有颜色,那只有这种颜色了。
过不去的永远过不去,即便有一天我们能够告慰那些无辜的殉难者。 但我还要感激你,怀着几近绝迹的虔敬向你说声:“谢谢啦,我的廖秃头!”
晓波
1999年11月24日于家中
我没回信,因为不知该说什么。 一个多月后,他写来第二封信,有如下内容:
...... 与其他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 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 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 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意强制),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 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质量。 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 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 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 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 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北岛不出国。 “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人的善良和坚韧是可以想象的,但人的邪恶与懦弱是无法想象的,每当大悲剧发生之时,我都被人的邪恶与懦弱所震惊。 反而对善良与坚韧的缺乏平静待之。 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为了在一片黑暗中让真实闪光,美是真实的凝聚点。 而喧嚣、华丽只会遮蔽真实。 与这个聪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欧洲那样,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陆地就是家园了。 我们是靠生命中仅存的心痛的感觉才活着,心痛是一种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状态。 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时,它仍然不识时务地喊痛; 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忆时,它记住那把泣血的刀。 我曾有一首写给刘霞的诗:“一只蚂蚁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脚步。 ”
我没见过你的姐姐飞飞,她该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你的笔使我爱上了她。 与亡灵或失败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 如果可能,你去扫墓时,代我献上一束花。
曉波於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

我还是不知该说什么。 我觉得坐一次牢已足够,而晓波却坐牢、反抗; 反抗、坐牢,翻来覆去,以减轻强加于己的幸存者负罪感。 我开始采写此书时,他是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天天在网上抨击党和政府。 2007年隆冬,他几乎重写了余世存起草的“颁奖辞”,要亲自授予我笔会的自由写作奖,酒店订好了,人也通知了,不料东窗事发,包括他在内的几十名在京笔会成员被控制在家,出不了门,而我被三个警察押送回四川。
不料至此永诀。
我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者。 后来他判刑、坐牢、获诺贝尔和平奖,我都没想到会是永诀。 我淡忘了他上述两封信,即使没淡忘,大约也不会将信中说的“道义巨人”和他挂钩,不会将遥远的甘地、耶稣、哈维尔和他挂钩,因为这个叫刘晓波的人太熟悉了。 永诀前夜,我们还围着火锅互相取笑,还约定二十年后一块隐居山野。 直到2011年我逃出中国,在德国出版此书,随后有了中、西、捷克、波兰文版,我还经常想起他。 最近三年多,经常和刘霞通电话,还绕着狱中的他打转。
他是打算坐穿牢底。 他与外界隔绝,对软禁的妻子深度抑郁,妻弟刘晖受株连被判11年徒刑一无所知。 直到今年3月末,我鼓励刘霞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他才首次知道比牢狱更残酷的现状,震惊之余,他立即答应陪妻子出国治病。
于是我给德国总理默克尔写信求援,德国驻北京大使随之致电刘霞,核实我在信中讲述的一切。 我以为很快就会见面——也许他不好意思,为了爱情而放弃在中国的坚守? 煎熬这么多年,世上最幸福的该是刘霞了......
可世事難料,他突然被查出肝癌晚期,保外就醫卻被嚴密監控。 劉霞趕過去,并冒險托家人致電我。 我給默克爾夫人寫了第二封信。 我轉達劇痛中的曉波“死也要死在西方”。
才20多天,他就走了。 此前我在给默克尔总理的密友Wolf-Biermann夫妇的信中写道:“他快不行了。 但他的临终愿望,还是来德国! 我知道他的想法,是用最后的生命护送他的妻子及妻弟来自由的德国...... 我家附近有柏林最美的墓地,中心有个水鸟飞翔的湖泊,他可以埋在这儿,我们也好经常去看他......”
但独裁者扣住不放,他们甚至害怕这个著名思想犯的骨灰。 他的信中骇然浮现“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 也许我正在被彻底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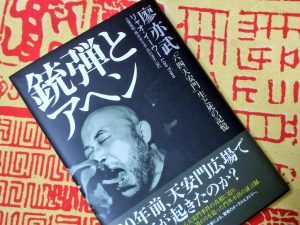
我明白,他,还有余志坚,还有此书记载的众多遇难者,都在天上俯视着。 我泣不成声地修订此书,愿上帝保佑能在天安门大屠杀三十周年时出版英文、法文和日文。

为此我感谢完整版的英译者David Cowhig(髙大伟)和Jessie Cowhig(髙秀华),您们付出的无私努力,将被历史铭记; 感谢蒋慧娜小姐,您首次试译数篇,文笔精湛; 感谢江晨欣小姐,您也曾译出《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发表之后广受好评; 感谢曹雅学女士,每当此书遭遇挫折,您的帮助总会带来转机,带来源源不绝的动力; 感谢《吆尸人》《上帝是红色的》《证词》英译者黄文,没有您,我的书和人都到不了西方; 感谢康正果、廖天琪、苏晓康、吴宏达、胡平、一平、陈迈平、余杰、余世存、王怡、蔡楚、北明、郑义、马少方、黄河清等朋友,没有您们,我的书和人也到不了西方; 感谢“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丁子霖和蒋培坤,晓波生前最敬重的两位,此书不可缺少的附录源于您们; 基于此,也感谢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发言人孙立勇; 感谢在全球率先推出此书初版的德国渔夫出版社和莫尼卡、彼得. 西冷、汉斯. 巴门斯,感谢德译者彼得. 霍夫曼夫妇 , 您们是我的翅膀,我始终如一的支撑; 感谢作家同行赫塔-穆勒、菲利普、萨尔曼-鲁西迪、张彦和侯芷明给予的精神温暖; 感谢台湾允晨文化总编辑廖志峰,我兄弟般的母语出版者; 最後要特別感謝我的纽约經紀人彼得. 伯恩斯坦和艾米,我这一点点成就也属于您们——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虽然语言不通。
八月 4, 2017 at 柏林夏洛特城區
廖亦武于July 12, 2024周五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