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多月前,我读了余东海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怀念刘晓波”。东海先生在文中说:哪里是我的祖国,哪里就必须自由起来。他还说:“让祖国自由起来,是我们这些后死者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东海先生所表达的心志,对我的脾性,对我的胃口。
前些天,我又读了野渡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那个打捞光明的结巴”。野渡先生在文中坦陈的“这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之信念,再次激起我的共鸣,并引发我的命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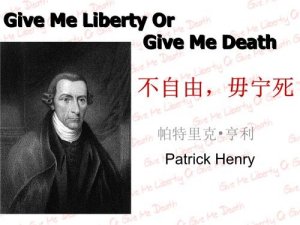
在自由与祖国的关系上,有一句话是深为打动人心、一直不胫而走的;那句话就是美国近代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Where there is liberty, there is my country)。按我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勇于追求自由的人,为了能享有做人的基本自由,尤其是为了摆脱严酷的政治迫害,他有权去国;这种去国,理直气壮,无可非议。即便他随后入籍他国,也同样理直气壮,无可非议。很显然,对于这种去国之人,“叛国”的帽子根本扣不上,“有奶便是娘”的指责,也完全站不住脚。爱因斯坦于1932年12月离开德国去美国,1935年5月正式提出定居美国申请,1940年10月入籍美国,1955年4月18日他的骨灰撒在美国——对此,除了纳粹政权和极少数脑子大量进水的人外,还有谁会说爱因斯坦是一个可耻的“德奸”,是一个人格上很不足道、谁给好处就投靠谁的见利忘义之徒?
从义理上讲,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不自由的国家,还存在由专制政权所施加的政治迫害,“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句话,就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然而,我说这句话没有过时,并不等于说人们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尤其是在地球上的右翼极权已经消失、共产极权已经蜕变为后极权的时代,人们作出其它选择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就我而言,我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去国抉择的同时,十分赞成和认同余东海、野渡的选择。多年来,我的志向、我的言说和我的行为是一致的,它们三者所表明和体现的,都是一个主旨:这里是我的祖国,这里就应当自由起来。
我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它似乎显得高尚些,而是基于现实的考量。我从不相信大陆中国人不配享有基本自由,也清楚心中向往自由的大陆中国人,事实上多得不可胜数。倘若世界上的自由国家不加限制、不设门槛,对前去移民的外国人能够统统照单全收,我想,保不齐会有高达上亿的国人跃跃欲试,将愿景化为行动。然而,世界上的自由国家虽然决不会设置禁锢本国国民的柏林墙,但无一例外都有入境限制和移民限制。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如有些人指责的那样,表明他们对人权原则的伪善和背离。这是因为:如同公寓处于管理者的监护之下和小区处于物业公司监护之下一样,自由国家处于其民选政府的监护之下。谁都知道,外人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公寓,更不能不受限制地留宿公寓;非小区业主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小区,更不能在小区空地上搭建小木屋供栖身之用。依据同样的道理,外国人也无权不受限制地进入任何他们想去的国家,更无权不受限制地成为他国的成员。入境限制和移民限制的严格存在,决定了不自由国家中能够通过去国获得自由的人,只能是占比极小的一部分人。于是乎,“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的名言,就不可能落实到不自由国家中绝大部分追求自由的人身上。
哪里有自由,但哪里我去不了,怎么办?
如果未曾绝望,如果不想苟活,如果依然想享有自由,那么就将自然地导向如下选择:这里是我的祖国,这里就应当自由起来。
诚然,让祖国自由起来,实非易事。但是,难,就不做了么?近200年来,在世界上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自由起来的国家,有哪一家碰上的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的历程?
有人说,让中国自由起来,更难。然而,更难,就要放弃吗?就要认命吗?就只能交由上帝或上天来解决吗?
更难所造成的,很可能是我们自己无法亲眼见证中国实现自由起来的全过程。但是,我们的后代呢?我们的后代会不会是壮丽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弄潮儿呢?
我相信是。
2019年7月30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7月31日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