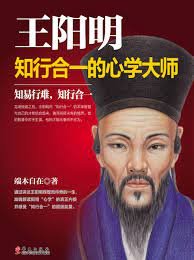
根据理论思路,我们可以把孔子学说区分为三个层次:中庸的道、作为忠恕的理和八德(注),道生理,理化八德,换句话说:我们履行道-理,我们最终能拥有仁义之德,成为谦谦君子,社会就秩序井然、歌舞升平。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型,比照现实社会,由于地区社群不同、迭代不同以及个体认知的思想差异性,必定会出现许多遵行的偏差,甚至是违反的情况出现,例如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恕之理,由于不同的人对自己不喜欢(不欲)的理解千差万别,则他虽然严守这一恕理,但他的活动(施于人)仍然为别人(对不欲有不同理解的)认为是被侵犯;更有甚者,有些人故意不守恕理,专门“己所不欲、也施于人”,为了达到利己的目的,采取的是谄媚巴结、谗言陷害等手段构害他人。从历史发展来看,随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和人口的增加,社会的复杂程度就会越来越高,特别是官场中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这种道德的偏差和政治上恶行也越来越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纠偏和纠错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説,在社会政治上,正义与邪恶永远处于动态的变动中,君子代表正义,是自小读圣贤之书的正派人群,理应是社会管理阶层中纠偏纠错的平衡力量,但遗憾的是,历史上的君子难以胜任这样的工作,从频繁的改朝换代中可以看出,历史往往并不是倾向君子代表的正义一边,反而是恶势力不断膨胀,最后竟是为祸百姓,致使社会崩溃。为什么会这样?以往许多研究者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作过深入的讨论,现在我们更应从理论方面来探讨一下其原因。
君子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他的道德规范来源于古代中国的封建制下形成的贵族精神,正如孔子总结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4.16),君子追求的是仁义这一精神和道德层面,与百姓所讲求的谋生功利不同,在解决君子之间或诸侯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形成了一套公开公平的决斗规则,决不会像民间通行的死缠烂打。所以,人们理解的君子就是谦谦君子,是“温、良、恭、俭、让”。所以,先秦时期的君子,往往要求言行一致,君子人格是通过君子的作为表现出来,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宋襄公在宋楚“泓水之战”的失败,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在泓水边发生战争,战争开始时,楚军要渡过泓水河攻击宋军,宋襄公率军在河边列阵等待,宋国军事官子鱼提出建议,趁敌军半渡而击,宋襄公拒绝了,认为这是乘人之危的做法,不是君子所为,有辱贵族精神和体面。后来敌军已渡但未整军容列阵时,子鱼再一次提请发动攻击,宋襄公再一次拒绝,只等到楚军列好阵开始才发动攻击,但因楚强宋弱,直接正面对决,结果只能是宋军大败。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时与势移,虽然都是周天子下的诸侯国,相比之下,楚国的体量巨大,人口众多,军队数量远远超过宋国,相对弱小的宋国根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同等列阵对决的,宋襄公思想固化,他的行为继续受自己君子规范的约束,最终只能败下阵来。
宋襄公的君子做派受后世不断的嘲笑,轻者受人讥笑为区泥于迂腐教条,殆误战机;重者则直接否定宋襄公尊行的仁义道德,韩非子抨之为“亲仁义之祸”,连二千多年后的毛泽东也用毛式言语评价宋襄公执行的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就是历史上难解的君子困局,这不但发生于诸侯的国与国,也常发生于个人身上,如孔子的弟子子路,亦受制于君子的约束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中记载:在卫国做官的子路,因卷入一次宫庭事变中,在与敌方博斗时,被敌方“以戈击之,断缨(帽带子)。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掉)。结缨而死。”在春秋时期开始,随着诸侯国之间的战事频仍,战争逐渐脱离贵族君子战法,公元前515孙子总结战争经验,写出了《孙子兵法》一书献给吴王,用于指导战争并取得胜利。孙子兵法早已放弃君子对决的公开公平原则,为了取得胜利而不择手段。但是,有君子素养的人们仍然拒绝认可这种改变,声称:“春秋无义战。”从战争的手段的非正义推导到战争目的之非正当,批判否定一切大小战争。
自秦已降,君子逐渐演变为有道德讲仁义的好人或好官,小人则由原来意指平民百姓变成坏人或奸官,在官场也好,民间也好,有道德修养的君子是竞争不过小人,因为小人有无数的没有道德底线的手段和办法,这些都是君子一屑不顾,更不会亲历体会,君子所擅长的是作道德文章,对皇上规劝、对时弊进行抨击、对坏人进行批判,所有的这一切,在权力和利益面前,是非常脆弱和无力的,而且还会因为小人在取得权柄后,就取得了裁决的标准制定权和裁决权,反过来黑白颠倒地判定君子就是坏人,坏人成了好人。所以,儒家标榜的“三纲五常”道德伦理往往难以张目,官场的生态就是“恶币驱逐良币”,从新皇朝开始时的“众正盈朝”经历区区几代人的洗礼,最后只剩下“奸佞之臣”、“平庸之辈”摩肩接踵地充塞于官路之上,政府无能、颓废、黑暗,离动乱倾覆就不远了,所以,皆因困于“动口不动手”和难以作为,君子往往只能坐困愁城,眼睁睁地看着社会的崩塌。
儒学标榜承继孔子的圣贤之学,以宋明理学的发展为巅峰,因吸收了佛学的影响,理学增加了神秘主义的色彩,内容庞杂难懂,大致可以总结为几点:“格物致知”、“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存天理灭人欲”。但满足于“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空谈性理轻视实务之风,不但㳽漫士林,而且影响了整个政治。”(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P.277)所以理学最终是流于纸面文章,成为专服务于科举的“举业”,取得功名后,多被抛弃不顾,或空谈于文字游戏,离孔子的济世治国的理想完全脱节。时至明朝的王守仁(号阳明,后世尊称王阳明)在自己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对这种荒谬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反思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与朱熹同时代学者陆象山思想暗合的心学理论,所以后世又称阳明心学为陆王心学。
王阳明创制心学过程与他的人生轨迹一样非常曲折传奇,从格竹子的理学认识挫折、到着迷于佛学和道学、再到科举得意和官场失意被贬贵州龙场,最后在困厄中顽强生存并在思想上不停思考和领悟,终于豁然开朗,到达新的思想境界,史称“龙场悟道”。阳明心学主要包括“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两大部分。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正是针对时弊而发,“知”就是“行”,没有“行”的“知”,也就是“不知”,例如我们认知了“孝”,如果不在现实生活中对双亲“行”孝,则可以说对孝还不认识。对“知行合一”的解读可以多方面多层次,但我们知道王阳明曾着迷于佛道,对佛道理论的很深的研读,所以他的演讲和述作都融会了佛道的语境和参道方式,所以我们应略去阳明心学中大量的神秘主义的表述和内容,从理性可理解的角度去解读,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并非似他表面上所说的是认识论的理论,如“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以反对朱熹注重于外界认知的“格物致知”,其实阳明心学更是一种方法论的理论,是达致事业成功的心理修养和方式方法的选用,真正作用就是要破解上述的千年未解的“君子困局”:以往道德君子往往是坐而论道,对政事或理想目标追求,以道德教化和规劝为主,多维护自己的名誉、爱惜“羽毛”,是知而不行,结果收效甚微。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事上练”,要首先“立志”,严于律己,忍受和克服挫折,围绕着工作目标,全身心投入,不能作壁上观或在旁评说,在做事的同时来认识和历练,从中提高认识水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事上练”中,不要讲求道德“洁癖”而自我限制,许多即使不是儒家的方式方法都是允许的,这些都是达致目标所必须的过程,达致目标、取得成功,比讲求方法的合道德性更为重要,也能心安理得,不要受到自己心理困扰,所以,君子不再受困于手段不济而空悲叹。
王阳明也身体力行了他自己的理论,不但在“立志立言”中花大力气,影响后世巨大,在“立功”中都有出色表现,在当时的赣南剿匪、平定朱宸濠江西叛乱、广西土司叛乱中屡建奇功,为他思想的影响作了有力的背书。但是,王阳明在这些“立功”中,与其説发挥了他的心学理论,不如说他站于一个新的纬度,超越当时的许多世俗约束,在立功过程中,他的目标明确,实行的方式方法措施不拘一格,奇计百出,虚虚实实,时而诚心仁义、时而诡诈、时而杀伐果断,例如王阳明在赣南着手剿匪之初,即强制推行“十家持牌法”,这是相当于复活了法家秦法的“保甲连坐法”,这是传统儒家痛批的秦法苛政,使儒家推崇的亲善宗族聚居生活的睦邻关系荡然无存,会深深败坏了世道人心,后世不易恢复。但王阳明实行起来没有一点心理负担,过后面对纯儒的指责也坦然面对,只因这些措施对剿匪有效,最后取得成功。
这些又深刻影响了心学传人,如今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徐价斗严嵩、张居正斗高拱的故事,也体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对读书人的思想解放作用。张居正师从徐价,而徐价受阳明心学江右学派门人聂豹影响,可以说徐价和张居正都受阳明心学的熏陶,也是其践行者。现在看来,徐价斗倒严嵩,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胜利;张居正半倒高拱则是有为战胜了平庸,但他们的手段并非是传统君子的方法,看上去与那些奸官并无区别,如严嵩为了长期独霸权力,方便自己卖官粥爵、贪污受贿,不惜对皇帝曲意迎蓬巴结;徐价为了扳倒严嵩,也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写下大量青词,以助皇帝修仙,各种拍马溜须博得皇帝欢心,邀宠不断,甚至不惜在严嵩面前服软和装孙子等等;张居正更为甚者,竟然与宫中太监结成一党,给过去这个政治盟友高拱栽赃嫁祸,以达清除政敌的目的。他们与严嵩、高拱之间并非私人仇怨之争,清除他们,正是为达到儒家追求的被泽苍生百姓的宏愿,严嵩专权乱政,对朝庭和社会危害极大,徐价扳倒严嵩后并不是大权独揽以求私利,而是将权力传之下一代有作为的官员,自己则致仕退休去了;在张居正一代,斗倒高拱有必要吗?这是有所作为与平庸的对决,虽然平庸不等同于严嵩式的谋私乱政,但事实也证明,平庸也是一种恶,就如明未任内阁首辅时间最长的温体仁,就是典型的庸官,《明史》将温体仁列入奸臣传,评曰:“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温体仁)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温体仁貌如张居正重现,无私清廉,但对皇帝只是唯唯诺诺,对政局应付了事,只爱权力,为保手中权力不坠而不停内斗排挤异己,致使晚明帝国的重要职位长期形同虚置,有研究者将温体仁列为明亡的原因之一,这虽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切中当时时弊,揭示了庸官为祸之烈并不亚于奸臣之类。张居正急于要施行“一条鞭法”等新政的改革方案,及早为百姓减轻负担,缓和社会矛盾;但高拱身居首辅要位,必然是新政的绊脚石,要等他退休再从首辅上退下来,十多年过去了,改革时机尽失,所以,从阳明心学看来,张居正踢开高拱的做法,乃是君子所为、是正义之事业。
这又会产生一个新问题:如果从形式上看,君子的这种“不择手段”与其他人争权夺利的倾轧权斗并无二致,君子在这种“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的权斗中,如何确保其正义性和正当性?很显然,只有成为君子才是这个前提保证,胸怀救世济民的君子,才能使行为与目的统一起来、实行“知行合一”,王阳明在后期也意识到这个重大问题,在后期不断成熟的理论中,他侧重发挥和完善了“致良知”的理论。
王阳明的“致良知”中,“良知”概念出自孟子论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与程朱理学倡导的“格物致知”相反,王阳明认为,“良知”来源人的本心,“至善者,心之本体”,“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那么什么是良知呢?王阳明具体论述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恒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悌,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撇开王阳明借助的许多佛道学说参悟体验的用语,从理性角度理解,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善恶之心、羞耻之心”,“致良知”就是自我发现和增大上述的各个“心”(良知),将每个人本有的良知掌握并发扬光大,同时戒除许多消极的东西(即灭人欲,或称灭私欲)如“懈怠、轻忽、浮躁、妒忌、愤怒、吝啬、傲慢、贪婪”等等(《示弟立志说》),即可以成就圣人(君子),在“知行合一”的活动中立于正义的不败之地。
从儒家理论体系的发展来观察,其实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理论目的是一致的,不论通过个人的“格物致知”还是内省的“致良知”,最终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私欲)”,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脉络来看,可以说两者是殊途同归。只是阳明心学更偏重个人的自省内视,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希望通过增强每个人的能动性来打破世俗形成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困局,通过对理学方法的反转来达到克服一直存在的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使正义力量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起到压制秩序偏差的作用,这可以说是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阳明心学起到了对儒家文化浸淫的中国为首的东亚知识阶层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如对日本近代化的思想催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以至后来学者总结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王学(阳明心学)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中国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说:“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也称:“我国(日本)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更有在日俄战争期间,率联合舰队大败俄国舰队日本的东乡平八郎深受阳明学的影响,尊崇王阳明。随身携带的一块腰牌上刻着“一生低首拜阳明”作为座佑铭。在近现代中国,许多历史人物,如维新派康梁;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国民党的汪精卫、蒋介石,共产党的毛泽东等人,在其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
那么,阳明心学究竟在那些方面对近代以来的历史人物发生影响?根据的研究显示:日本“阳明学”是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的借助阳明心学某些方面发起的一场社会思潮,既不是中国明代王阳明思想在近代日本的深化和再现,也并非学术思想流派,“他们皆以阳明学练习其心胆,高其气格,贯穿道理心肝,填补忠义骨髓,死生谈笑间,能成就撼天动地大事业。”(邓红《“日本阳明学”的真实与虚构》2018-02-24【光明网】)所以,阳明心学中对个人“立功”的修养功夫,是近现代相当一部分人来这时寻找的获取成功的思想利器,特别是在高风险高压力的领域,它是遇事应对时的准确判断力、坚强意志、偏执的信念和克服焦虑的平常心等等,这是王阳明式成功的必备心理素质。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説,后世许多人抛下了“致良知”的儒学理论内核,只取其中的立志和修炼意志的思想工具,嫁接到不同的理论之上,这也就可以解释了:虽然同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却不同的人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既有维新派又有革命派,既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
从近现代的实践看,阳明心学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历史上阳明心学造就了王阳明、徐价、张居正等许多能臣,虽有不少的出色表现,但对社会整体影响极其有限,理论上也不能取代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实践上则成为专制朝庭的利器工具使用,一旦力尽,即受专制体制反噬,个人或家族遭受迫害。当王阳明年老体弱、疾病缠身,无力再担任公职,一再提出退休致仕回家治病养老,朝庭却置之不理,最后迫得王阳明不顾一切,私自弃官夜奔回乡,竟客死半道,朝庭竟无半点怜悯之心,相反,朝廷下旨追究擅自弃官之罪,褫夺王阳明“新建伯”爵位,并下令禁止传播王学(阳明心学);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等新政成功,但死后也受到朝庭清算,皇帝下旨剥夺张居正一切称号,查抄和罚没家产,荆州老家饿死十七口人,长子上吊自杀,后来新政也形存实亡。所以,在专制体制和强大保守势力之下,靠个别能臣的道德修为和个人努力,根本不能达成“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其次,如果从“道统”理论角度来看,陆王心学仍与程朱理学等其他儒学处于同一传统思维层面,他们的共同特点仍是提倡个人的道德修养是社会治理的起点和手段,通过个人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努力、最终能达到“治国、平天下”,没有深入去研究和论证两者的因果关系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虽然他们都声称获得了“道”一级的终极真理,但遗憾的是,他们理论并没有达到“道”的层面,仍是位于“道”之下的“术”的层面,没有论及孔子推崇的认为“至道”的中庸思想,也就没法找到跨越个人修养与治国安邦两者鸿沟的桥梁。相反,儒家理学在明朝专制权力的催化下,逐渐形成严苛无情的礼教,对中国人的人性和文化进行压制和摧残。“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谭嗣同《仁学》)在当时的科举取士的体制下,如果一个读书人的看法或观点一旦被判为有违名教(礼教),个人前途就此断送,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读书人只能墨守陈规,不敢有自己的想法或越思想雷池半步,社会也随之僵化停滞不前了;在社会生活的范围中,礼教发展出各种反人道的限制,对各阶层的人性更是进行无情的摧残和压制,例如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断送了多少女姓追求幸福的权力。所以,以理学为中心的儒学,发展到最后,竟是“物极必反”,变成了对孔子治国济民理想的反动。
受王阳明思想影响或受议题启发的晚明清初学者,很多人开始打破理学的思想禁锢,将理论审视的目光投射到人性、社会体制和国家架构上。如王学后期弟子李贽将理论推演进行到底,在王阳明的“良知即天道”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人欲即天理,将天理和人欲两者对立和二者选一是错误的,完全否认理学礼教。黄宗羲的批判将这种反思中达到了最高的高度,他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专制政治,提出重返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认为帝王将相或“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或“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的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
再次,在近代的近代化改革大潮中,阳明心学确实对当时知识阶层如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有过巨大影响,但在理论能力上相当有限,实际上难以承担起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重任。从世界格局来看中国的近代史,中国在世界改革大潮中的位置并不落后,相反还有点领先的,1861年中国就开始了全国性社会改革性质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世界各国都在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运动:1861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超過2千3百多萬的農奴獲得自由,拥有公民權利,释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在其后的全面改革提供基础;美国于1861年开始打南北战争,到1865年结束,解放了南方各州黑奴,促进了全国工业的发展;日本于1868年才开始明治维新,国家开始转上经济和国力发展的快车道;德意志是1871年俾斯麦才开始执政,用铁血手段统一国家和推行国家近代化;法兰西经过普法战争之后在1872年开始法国大革命。结果,大多数国家的改革都取得成功,只有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了,当时士大夫以“中体西用”对抗西方的思潮和制度,但作为“中体”之一的王学与其他儒学一样,并不能使中国的面貌换新,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
最后,如果将阳明心学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则阳明心学就是一个思想工具,这就派生出许许多多的理论问题:为达成目标不择手段,打破君子困局,也解除了君子的传统道德约束,那么目标的合道德性要求是什么?目标的选择是否有正义性的制约?达致目标的方式方法是否有下限要求?等等。阳明心学作为一种思想工具,与其他的工具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不好,在施展刺向对手时,也会割伤自己,如果这些延伸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带来的消极影响就会是很大的,特别是受儒家影响的东亚国家,在科技先进的当代社会,有时消极影响甚至是灾难性的。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以追求国富民强为第一目标,深受王学影响的东川平八郞式的军人,在对外展开的争夺战中,投身到一个又一个的军事目标的争夺,不计代价地争取胜利,以1904年日俄战争中旅顺攻防战最为典型,日军主要以人海战术发动“万岁冲锋”,以士兵的血肉之躯冲击俄军的机枪阵地,一场冲锋往往造成日军伤亡几千人,日军前后发动10多次攻击,损失六万多人,真是触目惊心,最终竟也被日军攻占俄军据有的地区,击败俄国。目标达到了,似乎战死多少人都是值得,人命如草芥,变成为战争机器的一个个小齿轮小零件,后来日军军部竟绑架整个国家,将目标定得越来越大,战争不断扩大,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扩张的不归路,祸及广大东亚国家,直到最后在能量耗尽后倒下。国家是如此,作为国家的领导者也是如此,国家目标和达至目标的手段应受更普遍原则的制约,受到正义的“中庸至道”的制约,如果一国领导人经过艰苦奋斗,成就一国领袖后并不就此满足,还要确立更大的目标,以贫穷落后的一国之力去追求成为世界领袖,这样没有约束的空想目标必然带来灾难和祸害,历史证明也正是如此。所以,阳明心学不能仅止步于就此阅读,要超越心学理论,就要跃上高一个层面,进一步探讨孔子关于中庸之道对社会制度的基础建构和统领的作用,这样才能从理论上解决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注:参见我前几篇的分析文章。连接网址:
https://astudyofconfuciustheory.blogspot.com/



